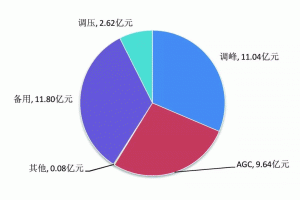電力輔助服務:從計劃到市場的演進
市場化建設從起步走向縱深
電力輔助服務管理工作關系到很多環節,涉及到發電側、用電側和電網端的技術發展水平,關系到電源結構、用電結構以及電網的調節能力,也關系到整個電力行業的市場化水平,尤其是電力輔助服務交易又屬于電力交易,與電量交易相比,更講究實時性,因此說,電力輔助服務交易先天屬于現貨交易。種種因素疊加,讓電力輔助服務市場建設變得尤其艱難,過程也尤其漫長。“總體來講,我國輔助服務市場發展相對緩慢。”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常務副理事長俞振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表示。
2017年11月,《完善電力輔助服務補償(市場)機制工作方案》要求,“實現電力輔助服務補償項目全覆蓋。43號文中規定的項目應全部納入電力輔助服務補償范圍。部分地區自動發電控制、調峰等服務未進行補償的,要補充完善區域并網發電廠輔助服務管理實施細則相關規則條款,并切實落實到生產運行中”。
我們知道,43號文是在2006年印發的,也就是說,11年前規定的一些輔助服務補償項目到11年后竟然還未得到落實。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電力輔助服務市場化改革的復雜程度,同時也決定了電力輔助服務市場化改革不能一刀切,須因地制宜。
其實,電力輔助服務市場化改革與其他電力體制專項改革在方向和路徑上并無二致,也是本著試點探索的原則逐步推進。各地在把握市場化基本方向的基礎上,在交易品種、市場主體、交易方式等體現市場化程度的具體方面又各有不同的特點。
根據各地方案和規則來看,在市場主體選擇方面,各地在發電企業的基礎上,大部分都考慮并納入了用戶和獨立第三方。福建和山西還納入了售電企業。華北和山東暫未納入電力用戶。而廣東和湖南因分別先行開展調頻輔助服務市場化交易和抽水蓄能輔助服務專項市場交易,也暫未考慮電力用戶,但廣東納入了獨立第三方。
同時,火電機組以其裝機容量占比大、一次能源經濟性好、能源轉化過程的精準可控和穩定,決定了其成為調峰機組的不二選擇。在電力產能過剩、煤電利用小時數下滑、煤價高企的背景下,積極提供電力輔助服務成為火電尤其是煤電企業扭虧的重要抓手。這就是電力市場的“神奇”之處,有時候你越是少干活,得到的報酬反而越多。而出力超過有償輔助服務補償標準的火電、核電和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發電,則是輔助服務費用的主要分攤對象。考慮到光伏占比微乎其微,東北地區只有風電參與輔助服務費用分攤。
在交易品種方面,除廣東和湖南外,各地在市場初期均是圍繞調峰和調頻開展交易,然后向無功、備用和黑啟動方向擴展。
在交易組織和交易方式方面,華北調頻輔助服務市場以省網(控制區)為單位開展,報價周期根據電網實際調頻需求容量的變化確定,采用集中競價、統一出清、邊際價格定價的方式開展;華北地區省網調峰市場采用日前集中競價、日內統一出清的日內市場方式開展。山西省調頻輔助服務市場采用集中競價、邊際出清、統一價格的方式組織;深度調峰交易采用雙向報價、集中競爭、滾動出清、統一價格結算的方式。山東調頻調峰輔助服務市場為日前集中競價,日內按照“價格優先、時間優先、按需調用”原則調用的方式組織。湖南抽水蓄能輔助服務專項市場采用雙邊協商交易和要約招標兩種方式進行交易。
但是,仔細觀察一下各地方案和細則,就會發現當前所說的電力輔助服務市場還不能稱之為真正的市場。各地現行的輔助服務市場中,一般都是采取賣方報價、競價,調度方根據價格由低到高依次調用,最后將費用平均分攤給納入輔助服務補償機制范疇的其他發電商和用戶。這顯然不如多買多賣的市場來得更高效、更公平合理。況且,并非交易主體的調度方卻擁有對服務提供者的選擇權,而最應該擁有選擇權的輔助服務費用支付方卻只能被動分攤。這里面或多或少還存在非市場的影子,還明顯算不上最理想的市場。
其實,就大部分輔助服務交易品種來說,完全可以借鑒配額制,比如在電網低谷時段,調度機構根據系統負荷計算出所有納入輔助服務補償機制范圍內機組的平均降出力比例,作為相關機組的輔助服務配額,逾期完不成配額的機組就會被考核。一些具備條件的機組或者說靈活性較好的機組在完成自身配額指標的同時,可以進一步報價出讓自身的降出力指標(直至停機備用),而那些沒有降出力意愿的機組可以根據市場情況報價購買這些指標,來沖抵自身承擔的輔助服務配額。同樣,電儲能和可中斷負荷、第三方等也可以參與市場報價,向那些沒有降出力意愿的機組出售輔助服務。在電網高峰時段也同樣如此,只不過這時候需要的是用戶的降負荷服務并承擔降負荷配額,用戶除了自己消化這些配額外,還可以向發電廠、其他用戶、可中斷負荷和電儲能、第三方等購買服務來沖抵配額。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配額為基礎催生出的多買多賣的交易市場,也更容易與未來的現貨市場接軌。
作者:劉光林 來源:中國電業 責任編輯:jian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