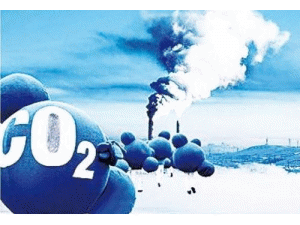CCUS:碳中和目標下亟須“綠動”
日前,生態環境部提出未來10年我國將開展二氧化碳排放達峰行動,有關工作將納入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查,并對各地方進展情況開展考核評估。這是在我國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后,所出臺的一系列二氧化碳排放嚴管措施之一。除了要嚴管外,二氧化碳“善用”
日前,生態環境部提出未來10年我國將開展二氧化碳排放達峰行動,有關工作將納入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查,并對各地方進展情況開展考核評估。這是在我國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后,所出臺的一系列二氧化碳排放嚴管措施之一。
除了要嚴管外,二氧化碳“善用”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而碳捕集、利用與封存(以下簡稱CCUS)作為解決我國以煤為主能源體系低碳化發展的重要戰略性技術之一,正成為當下的研究熱點。
“煤基工業和燃煤發電行業減排二氧化碳是當前我國減排的關鍵,而CCUS是目前唯一能夠實現大規模減排的技術手段。”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綠色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張九天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我國在未來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進程中,CCUS 技術不可或缺。而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提出,也給CCUS這一重大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CCUS技術不可或缺
對于CCUS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重要性,目前學界已達成共識。中國科學院武漢巖土力學研究所研究員李琦直接引用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綜合評估》結論中的一句話:“如果沒有CCUS,絕大多數氣候模式都不能實現減排目標。更為關鍵的是,沒有CCUS技術,減排成本將會成倍增加,估計增幅平均高達138%。”
在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暖之際,國際能源署近日發布的《CCUS在低碳發電系統中的作用》報告也指出,CCUS技術是化石燃料電廠降低排放的關鍵解決方案。“如果不用CCUS,要實現全球氣候目標可能需要關閉所有化石燃料發電廠。”
“CCUS可捕集發電和工業過程中使用化石能源所產生的多達90%的CO2,防止其進入大氣,而當前尚無其它成熟技術可達到如此高的脫碳水平。”張九天告訴《中國科學報》。
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何建坤介紹,從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到實現碳中和,歐洲有7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約50年的時間,而我國只有30年的時間。“所以我國每年碳排放下降的速度和減排的力度要比發達國家大得多,任務也更加艱巨。”
因此,在新目標下,發展CCUS技術就成為當下業界熱議的話題和研究方向。
自2006年以來,CCUS就被列為中國中長期技術發展規劃的前沿技術,并得到國家科研資金的大力支持。張九天發現,2006年至今,中國給予CCUS的研發資金支持從未中斷,支持資金面向自由探索、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和工程示范等多個階段,覆蓋包括捕集、運輸、利用和封存在內的全流程技術鏈條,形成了比較廣泛和穩定的 CCUS 研究隊伍。
然而,雖然CCUS在我國已有近20年的發展,并初步形成CCUS發展的技術體系,但在新目標下,CCUS技術在不同領域的結合還將會產生新的技術組合。
“善用”更為關鍵
“人人都知道二氧化碳資源化利用,關鍵是要找到好的切入口。”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常務副校長丁奎嶺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二氧化碳是惰性分子,惰性到可以用來滅火,“在溫和條件下讓它發生化學反應太難了”。正是在國家科研資金的支持下,丁奎嶺帶領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所研究團隊從2001年開始便在二氧化碳的世界里不斷探索。
直到去年,丁奎嶺團隊歷經近20年的基礎研究,開發了二氧化碳催化轉化合成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新催化劑體系、成套新技術,建成了全球首套千噸級中試裝置。
據丁奎嶺介紹,與過去以一氧化碳為原料的工業化技術相比,新工藝原料成本更低且來源豐富,“三廢”排放大幅減少。由于新工藝使用二氧化碳和氫氣為原料,對于富余氫氣和二氧化碳的行業與企業,不僅可以產生顯著的經濟效益,還將同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種延長產業鏈和提高競爭力的選項。
縱觀全球,關于CCUS技術的相關研究也是從2000年左右開始。科技部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研究員張賢等學者系統統計與分析了2000至2020年來自Web of Science 數據庫中CCUS相關科學文獻,結果發現,全球主要機構中,美國能源部、中國科學院和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對CCUS技術的研究實力和投入遠遠高于其他機構,其出版總量占全球出版總量的10.01%。
張賢介紹,中國學者于2004年發表了第1篇CCUS相關文章,發文量自2009年迅速增加,并于2016年超越美國成為年發文量最多的國家。遺憾的是,中國發文篇均被引頻次較低,中國相關文章總體影響力有待提升。
他同時指出,2016年以后,二氧化碳利用途徑和利用方式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加,“CO2 利用”成為熱點研究領域。其間,生物能源、負排放、生物質能結合碳捕集與封存技術等關鍵詞熱度迅速上升,CCUS技術經濟性研究熱度也不斷攀升。
“在現階段氣候變化影響逐漸加劇、二氧化碳減排日益緊迫的情況下,CCUS技術結合生物能源的負排放技術將成為未來研究重點。”張賢說。
目前關于CCUS 技術尤其是二氧化碳資源化利用的論文鋪天蓋地,但丁奎嶺希望涌現更多讓企業感興趣、用得上的技術方案。
急需構建新技術體系
在當下,張九天認為,我國應該考慮構建面向碳中和目標的CCUS技術體系。
“過去學者定義CCUS技術時,往往因為減排目標難以定量,而大多從科學角度進行分類,且分類的角度也比較多元化。”張九天表示,隨著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逐漸提高,CCUS的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發展,CCUS技術在不同領域的結合會產生新的技術組合,且主要是在捕集端有所不同。他提出,面向碳中和目標按捕集的二氧化碳源進行分類。
張九天進一步解釋道,具體分類包括:一是將化石能源燃燒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作為捕集的碳源,面向人類活動特別是能源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可稱之為FECCS;二是將生物質能源使用產生的排放作為捕集的碳源,這個碳源的捕集開始介入自然界的碳循環過程,即生物質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稱為BECCS;三是直接將大氣作為捕集的碳源,是典型的負排放技術,可稱之為 DACCS。
但就全球而言,國際能源署發布的上述報告顯示,碳捕集在發電領域的進展并未達到預期。報告指出,在運行的2個大型CCUS項目和在建的20個項目,預計總碳捕集能力將達到5000萬噸/年,但國際能源署可持續發展情景中到2030年電力碳捕集能力須達到3.1億噸/年,CCUS的發展尚未步入正軌。
張九天表示,當前很多國家都提出了碳中和目標,CCUS與相關能源系統的結合有可能培育出CCUS發展的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如集成CCUS技術與氫能生產技術系統、CCUS與可再生能源和儲能系統集成可行性與發展潛力等。
但由于CCUS技術鏈條比較長,應用的領域范圍比較寬,技術路徑應如何配置,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同時,緊密結合碳中和目標下我國煤炭、電力、工業等領域能源結構的變化,還需要考慮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中和的問題。
在碳中和目標提出之后,另一個問題不容忽視,即國內順應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而禁煤的呼聲和趨勢漸長,國內控煤措施趨緊,電力和工業部門為此提出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以替代煤炭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張九天提醒,不要誤認為CCUS技術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隨著煤炭的逐步替代而減少,CCUS在難脫碳的工業部門和負排放領域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作者:秦志偉 來源:中國科學報 責任編輯:jianping
太陽能發電網|m.www-944427.com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