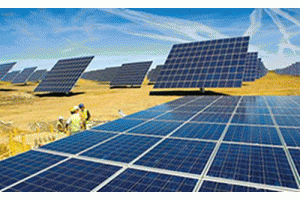清潔取暖工程鼓勵社會資本加入,現行電價政策成“攔路虎”
人到中年的劉國斌,2016年從某大型能源央企辭職后,自籌1億多元,創辦了位于北京西五環的北京燕開能源技術有限公司(下稱“燕開能源”)。而讓他“孤注一擲”的,正是當年剛剛興起的電代煤項目。
“在電力裝機本就過剩的情況下,低谷電更是供大于求。加上棄風棄光日益嚴重,通過蓄熱技術將谷電、棄電儲存起來,應用于北方供暖,市場大有可為。”劉國斌首先將目光鎖定在北京房山,第一年便砸下近40萬平方米電代煤項目,被業內稱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但事情并不遂劉國斌的心愿。本以為很快就能收回投資成本的項目,運行起來后,收益卻遠低于預期。為何會出現這種問題?癥結何在?劉國斌認為,問題就出在電價政策上。
“第一個吃螃蟹”的煩惱
正如《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規劃(2017-2021年)》明確鼓勵的,社會資本正在成為清潔取暖改造的主力之一。其中不少企業瞄準時機,紛紛希望通過電采暖工程分一杯羹。由于當時尚處起步,社會資本參與電采暖的成本不低。劉國斌介紹,僅房山區一個3.6萬平米項目,初投資就達1000多萬元。“作為回報,相關部門與我們簽下20年長協,算起來最多7-8年即可回本,預期效益理應可觀。”
但情況卻有些事與愿違。“第一年打基礎,收益不佳可以理解。但2017-2018年采暖季過完,經營非但仍無明顯改觀,甚至遠低于預期。有的項目采暖費收上來剛剛夠繳電費,一項成本就占到運行總數近90%。”劉國斌稱。
現行電價政策中,暫未對企業參與“煤改電”進行單獨說明,現階段多按一般工商業電價收取。劉國斌認為,問題正出在了這里。“北京大工業谷電價格現為0.3669元/千瓦時,相比居民谷電0.3元/千瓦時的標準,高出近7分錢。再加上企業需繳的基礎容量費等,相當于每度電成本0.55元左右。”
記者進一步從北方多地獲悉,類似燕開能源的情況并非個案。“在部分城鎮、棚戶區等集中供暖無覆蓋的地區,通過企業運作實現電采暖。居民仍按集中供暖價格繳費,參與企業卻執行一般工商業電價。像在山西,不滿1千伏谷電為0.4068元/千瓦時、平電0.6962元/千瓦時,不少企業稱很難承受。”日前在第二屆電能供暖產業發展論壇上,山西省經信委能源處處長高道平無奈坦言,“雖然大家都想盡快解決這一問題,但針對社會投資運營的居民采暖項目到底執行何種電價,我國目前仍未出臺明確政策。”
到底高不高?還能降低嗎?
從電代煤推行之初,電價爭議便已四起。電價,究竟如何成了影響電代煤“C位出道”的制約?
“其實,我們一直在探索降低電取暖成本的措施,現已推動14省市出臺峰谷分時電價、7省市出臺電價補貼、4省市明確了配套電網補貼政策。但即便如此,‘煤改電’項目仍普遍存在電價倒掛的現象。”國家電網有限公司營銷部副主任徐阿元指出,由于交叉補貼嚴重,價格難以合理反映成本,這與降低一半工商業用電成本的要求也存在矛盾。
同時,電網企業也面臨壓力。“無論前期配套電網建設,還是后期運維、服務,電網都承擔著不小成本。僅增容擴建,戶均改造成本就在2萬-2.5萬元,工程密集、規模大。再如,配套設施因大多僅在冬天使用,難以有效收回投資,長期持續投入將給企業經營帶來困難。”徐阿元稱。
作者:朱妍 來源:中國能源報 責任編輯:jian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