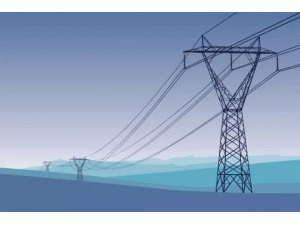新型電力系統構建需要全新的底層邏輯
2020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約110億噸,其中能源行業約占80%,電力行業碳排放占能源行業的比重超過40%。這使得“能源行業是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主戰場,電力行業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主力軍”的說法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不少地方政府將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責任主體鎖定在能源電力行業上,將發展重點聚焦
2020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約110億噸,其中能源行業約占80%,電力行業碳排放占能源行業的比重超過40%。這使得“能源行業是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主戰場,電力行業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主力軍”的說法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不少地方政府將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責任主體鎖定在能源電力行業上,將發展重點聚焦于超常規大規模發展新能源上。同時,多數發電企業也提出了宏偉的新能源發展目標,對風光等新能源資源新一輪跑馬圈地成為有關各方的首要任務,致使能源電力企業主動或被動承擔了實際上可能無法承受的發展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具有鮮明的國家基礎戰略特征,這既是我國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國擔當和實際行動,更是我國在新發展階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人民生活品質持續提升與社會全面轉型發展,積極適應全球市場競爭規則的重大變化,以及全面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戰略決策部署。因此,絕不能因為能源電力行業擔任碳減排的主要角色,就將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單一或主要理解為能源革命。因此,筆者認為,在當前的實際工作中,應堅持系統觀念,透徹研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與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底層邏輯,科學推進并不斷迭代優化。同時,也需將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的新型電力系統演進的底層邏輯研究提上日程。
產業系統與能源系統的關系
由“保障供能型”變為“互驅發展型”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邏輯,是通過推動各行業加速從高碳排放的技術路線轉換到低碳、零碳排放的技術路線,實現技術與產業的跨越式進步。這將推動各行業生產用能方式發生根本性轉變,由主要消耗化石能源變為全面使用可再生能源,由較低的能效水平變為更高的能效水平,產業系統與能源系統的關系也將由“保障供能型”變為“互驅發展型”。同時,用能方式的轉變將推動我國能源結構根本性調整。
也就是說,包括能源電力在內的各行業跨越式、壓縮型的產業升級,會經由生產用能方式的根本性變化傳導到能源電力行業,通過用能方式和能源資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變化,自然形成“能源行業是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主戰場,電力行業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主力軍”的能源發展新格局。
需要強調的是,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源”“目標”和“產出”,經濟高質量發展引導和推動能源高質量發展是“流”“手段”和“成本”。
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初心和使命是推動包括能源電力行業在內的產業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而不能單一理解為推動能源電力行業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和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
事實上,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和新型電力系統不僅是能源電力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具體內容,也是我國產業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機組成。同時,只有深刻理解各產業升級的經濟和技術規律、產業和能源的新型互動關系,才能真正找到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和新型電力系統的有效路徑。
能源結構調整
需最大限度通過“電為載體”實現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推動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和能源高質量發展,呼喚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將推動我國各產業的核心技術路線從高碳排放轉換到低碳、零碳排放,這要求必須實現能源消費結構的根本性轉變,即由主要消耗化石能源轉變為全面使用可再生能源,這種能源結構調整需要最大限度通過“電為載體”實現。
同時,要實現綜合能效水平的持續大幅提升,需要最大限度通過“電為載體”實現;產業系統與能源系統的關系由“保障供能型”轉變為“互驅發展型”,也需要最大限度通過“電為載體”實現。
技術進步的低碳化、零碳化,必然導致全社會生產用能方式高水平、高質量的廣泛電氣化。同樣,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高比例開發與高水平、高質量使用,以及不同能源的多元發展、協調互濟和源網荷儲的協同發展、優勢互補,都離不開高水平、高質量的廣泛電氣化。如此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勢所必然。
離不開全新的技術創新、
政策安排和激勵機制
與現有的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電力系統相比,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的目的是電能生產和消費系統實現零碳(近零碳)排放,技術、經濟約束將發生根本性變化。
從生產用能特性來看,因為各產業都需要廣泛使用可再生能源、持續提升能效,同時能源電力行業需要大規模開發可再生能源,這使得能源開發與利用必然是分布式與集中式并重,“電從節約來、電從遠方來、電從身邊來”三者并舉。相比之下,分布式更為基礎和廣泛,集中式則更能保證數量貢獻。因此,從提升綜合能效與系統能效入手實現節約能源、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將成為政策研究的重點、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安全特性和技術約束來看,隨著以新能源為主體的進程演進,電力供應安全和運行安全特性將發生質的變化。隨著新能源占比提高,供給將出現電量充裕而部分時段電力緊缺的情況,因此,需加快發展有效的電量“搬運”技術。同時,現有電力系統快速擴張發展取得的增加系統慣量、縮短電氣距離(提升短路容量)、增加動態無功補償能力的作用將被新能源大規模接入逐漸“中和”,同樣需要發展新技術去“補償”。
與現有電力系統相比,新型電力系統的技術體系將由以源、網技術創新為主向源、網、荷、儲全鏈條技術創新全面延伸,由以電磁輸變電技術為主向電力電子技術、數字化技術全面延伸,由單一的能源電力技術向跨行業、跨領域的技術協同轉變。
從成本特性和經濟約束來看,隨著以新能源為主體的進程演進,我國經濟發展合理的綜合用能成本將需要全新的控制策略。雖然光伏、風電的成本顯著下降,在發電上網環節可以與化石能源同臺競爭,但新能源接入電網的成本并不是終端用戶的電能成本。當新能源成為主體時,快速上升的系統平衡成本、安全保障成本等將逐漸成為主要的增量成本。
由此可見,新型電力系統的成本變化將對市場調節和政策調節提出更高要求,要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著手,找到經濟、安全、清潔三者的平衡點。因此,要保證能源安全約束條件下的社會用能經濟性,需要全新的技術創新支撐、政策安排和激勵機制。
(作者系國網(蘇州)城市能源研究院院長)
作者:李偉陽 來源:中國能源報 責任編輯:jianping
太陽能發電網|m.www-944427.com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