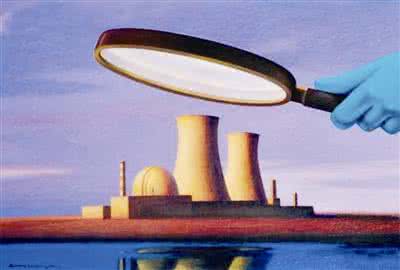能源法應該重在調控而非監管
●我國當前能源領域的主要問題,更多反映出的是能源市場宏觀層面的總量問題、結構問題和區域問題等,這給能源調控立法提出了多重任務。從問題導向看,能源法立法應該重在調控,而不是監管。
●我國現行能源法律體系一直沿用監管型立法路徑,試圖通過能源法完成從多頭監管體制向統一監管體制的轉型,既無必要也不現實。可通
●我國當前能源領域的主要問題,更多反映出的是能源市場宏觀層面的總量問題、結構問題和區域問題等,這給能源調控立法提出了多重任務。從問題導向看,能源法立法應該重在調控,而不是監管。●我國現行能源法律體系一直沿用監管型立法路徑,試圖通過能源法完成從多頭監管體制向統一監管體制的轉型,既無必要也不現實。可通過對現行監管立法的統一修改,并在多頭監管中建立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解決實踐中監管沖突和監管真空問題。
●應通過能源法確立能源產業調控體制機制和調控原則,合理引導和規范市場主體的能源生產與消費行為,優化能源結構,促進能源技術創新,提高能源生產和利用效率,促進能源產業可持續發展。
2015年4月,國務院立法工作計劃將能源法列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急需項目。同年6月,這部法律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二類立法項目。目前,該立法項目正在深入推進過程中,其送審稿及其修改稿正在不斷征求各方面意見。
在現有能源法律體系中,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能源法仍是普遍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筆者認為,在能源法的體系化過程中,我國能源市場的發展亟須補入的不是一部“大而全”的能源市場監管法,而是一部旨在總量調控、結構調控、區域調控的產業促進型能源調控法,即將能源法定位為能源調控法更為可取。
立法取向應直面能源問題的宏觀性
能源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能源供應和安全直接關系到國計民生與國家戰略競爭力。基于能源對經濟安全與社會公眾生活的至關重要性,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一直把能源首先作為一種基本公共服務來提供,其次才將其作為一種商品來進行監管。
歸納起來,我國當前能源領域現存的主要問題是:能源領域的結構性、體制機制性等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傳統能源產能結構性過剩問題突出,可再生能源發展面臨多重瓶頸,天然氣消費水平明顯偏低與其供應能力階段性富余問題并存,部分地區能源生產消費的環境承載能力接近上限,電力、熱力、燃氣等不同供能系統集成互補、梯級利用程度不高,跨省區能源資源配置矛盾日益加劇,等等。
凡此種種,更多反映出來的是能源市場宏觀層面的總量問題、結構問題和區域問題等,這給能源調控立法提出了多重任務,需要能源法作出積極回應,并增加制度供給。可以說,從問題導向看,能源法應該重在調控,而不是監管。
避免監管立法的簡單重復
能源法的制度設計是中國能源法律制度與其他法律制度相連接的起點與歸屬,直接決定中國能源法律制度績效與制度成本之比,決定中國能源法律的制度結構。能源法律制度結構的形成與完善,必須立足于我國能源市場發展和能源法制體系化的客觀現實。
不少人提出,應將能源法定位為市場監管型的能源基本法,以此區別于《煤炭法》、《電力法》、《礦產資產法》、《可再生能源法》等能源單行法。但筆者對此持不同看法。我國現行能源法律體系一直沿用監管型立法路徑,并已在諸多立法中確立了“多頭監管”的能源管理體制。試圖通過能源法完成從多頭監管體制向統一監管體制的轉型,既無必要也不現實。通過對現行監管立法的統一修改,并在多頭監管中建立有效的監管協調機制,是解決實踐中監管沖突和監管真空問題的可行路徑。
能源的安全、有效和持續供給以及能源結構的科學調整與節約利用,應是能源法律制度是否獲得合理安排以及評價其實施效果的重要標準。在產業結構、經濟增長方式、政府管理機制、社會平衡模式與自然生態體系等方面,能源法需要區別于現行立法,并真正發揮其應有的調控作用,以立法轉型真正帶動能源發展的戰略轉型。
能源法需要促進能源的市場化改革,放松對能源市場的政府管制,在激勵競爭中著力提高能源供給效率和生態效益,改變能源供給結構并優化用能方式,最終實現節能減耗與清潔環保的目標。
作者:席月民 來源:經濟參考報 責任編輯:wutongyufg
太陽能發電網|m.www-944427.com 版權所有